刘永川博士 Dr. Alex Liu (Yong-chuan Liu)

 我是1986年6月20日离开北京到了美国加州,先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学习了一个暑期的英文与美国文化,之后在
1986年10月入学斯坦福大学,1992年3月31日完成了全部学业工作,期间我在1989-1990学年休学了一年,所以在斯坦福大学一共学习了4年半,不算太长。但完成学业后,我在斯坦福大学的亚太研究中心做过将近一个学年的博士后研究,之后还在胡佛研究所兼职做过一点政经技术医疗系统的比较研究。加上后来的几年就住在斯坦福附近,感觉在斯坦福大学呆了很久似的。
我是1986年6月20日离开北京到了美国加州,先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学习了一个暑期的英文与美国文化,之后在
1986年10月入学斯坦福大学,1992年3月31日完成了全部学业工作,期间我在1989-1990学年休学了一年,所以在斯坦福大学一共学习了4年半,不算太长。但完成学业后,我在斯坦福大学的亚太研究中心做过将近一个学年的博士后研究,之后还在胡佛研究所兼职做过一点政经技术医疗系统的比较研究。加上后来的几年就住在斯坦福附近,感觉在斯坦福大学呆了很久似的。

 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学习经历和北京大学的经历还真有许多类似,可能是在同一个“服务之灵”的带领之下,很多人记得我的都是我那些代表留学生“为人民服务”而当仆人的“伟绩”。比如在1987年把斯坦福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ACSSS
活跃起来了,一起设立了一个定期的斯坦福社会发展议题论坛,代表斯坦福中国学生与旧金山湾区许多华人组织机构建立联系、并开始合作,1989年又代表斯坦福中国学生参与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并担任了第一届主席,为此而参与了一些特别而又影响重大的决策、并有机会做了一些特别的协调领导工作,之后再代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去协调组织全球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等等。回想起来,这些都是当时的一些开创性的工作,所以产生的社会影响很大,和我当时的精神追求紧密相连,或许也影响了我对数据分析支持之决策系统的兴趣。
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学习经历和北京大学的经历还真有许多类似,可能是在同一个“服务之灵”的带领之下,很多人记得我的都是我那些代表留学生“为人民服务”而当仆人的“伟绩”。比如在1987年把斯坦福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ACSSS
活跃起来了,一起设立了一个定期的斯坦福社会发展议题论坛,代表斯坦福中国学生与旧金山湾区许多华人组织机构建立联系、并开始合作,1989年又代表斯坦福中国学生参与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并担任了第一届主席,为此而参与了一些特别而又影响重大的决策、并有机会做了一些特别的协调领导工作,之后再代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去协调组织全球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等等。回想起来,这些都是当时的一些开创性的工作,所以产生的社会影响很大,和我当时的精神追求紧密相连,或许也影响了我对数据分析支持之决策系统的兴趣。
 1986年秋进入斯坦福大学,我是到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相对其它大学而言,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系比较小,我当时申请该系是因为对那里的两位社会学教授的社会动态模型工作极其感兴趣。到校以后,我却发现其中一位教授已经离开了,留下的那位知名教授TUMA平时比较忙、而且她往下的研究方向与我的期望很不同,她当时的研究偏向区域内的动态指标的数据估值。系里还有两位定量研究方法的年轻教授则还在起步阶段,我感兴趣的他们都没兴趣或者不懂,弄得我当时是刚入学就想转学了。记得曾有一位中国科学院的博士也和我一样向往斯坦福的社会动态模型,比我晚一年来到斯坦福,他在斯坦福社会系呆了不到一年后就转学去了哈佛大学。我当时主要是考虑到转学费时费力,而且我慢慢也喜欢上了斯坦福校园和旧金山湾区,为此就打消了转学的念头,觉得或许转系更容易些、更可行些。
1986年秋进入斯坦福大学,我是到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相对其它大学而言,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系比较小,我当时申请该系是因为对那里的两位社会学教授的社会动态模型工作极其感兴趣。到校以后,我却发现其中一位教授已经离开了,留下的那位知名教授TUMA平时比较忙、而且她往下的研究方向与我的期望很不同,她当时的研究偏向区域内的动态指标的数据估值。系里还有两位定量研究方法的年轻教授则还在起步阶段,我感兴趣的他们都没兴趣或者不懂,弄得我当时是刚入学就想转学了。记得曾有一位中国科学院的博士也和我一样向往斯坦福的社会动态模型,比我晚一年来到斯坦福,他在斯坦福社会系呆了不到一年后就转学去了哈佛大学。我当时主要是考虑到转学费时费力,而且我慢慢也喜欢上了斯坦福校园和旧金山湾区,为此就打消了转学的念头,觉得或许转系更容易些、更可行些。
 留在旧金山湾区,留在硅谷,也确实带给了我许多额外的特别经历和收获,让我的留学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了许多。一是有机会参与许多社会活动而结交许多杰出朋友,二来有机会学习硅谷科技发展,同时也得到机会去了解各种宗教信仰。我是在斯坦福校园有了人生第一次的参与基督教会聚会的经历,也曾参与几次多宗教比较的信仰讨论,并在台湾参访时会见了星云大师、到佛光山探讨佛教与人生。
留在旧金山湾区,留在硅谷,也确实带给了我许多额外的特别经历和收获,让我的留学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了许多。一是有机会参与许多社会活动而结交许多杰出朋友,二来有机会学习硅谷科技发展,同时也得到机会去了解各种宗教信仰。我是在斯坦福校园有了人生第一次的参与基督教会聚会的经历,也曾参与几次多宗教比较的信仰讨论,并在台湾参访时会见了星云大师、到佛光山探讨佛教与人生。
 而在社会学系,我也还是得到了一些特别的学习机会,受益良多。我做过好几次社会学定量研究方法课的助教,也做了TUMA教授的助研而让我学到很多,特别是小区域数值估值的一些方法,尽管那不是我最感兴趣的。同时,我也为好几位教授做过数据分析的助研。其中有一位教授还曾说,我给他当助研而出来的文章是他这辈子发表的最好的定量分析文章。相对而言,斯坦福非常开放也经费充足,拿到博士资格后至少有五年时间不用担心资助问题,可以完全按兴趣发展。尤其是社会学系根据我以前的学习经历和研究方法与统计的相对高能力还免去了我必修的几门课程,这就给了我机会到统计系、计算机系和其它系去学习和交流,结果我修了一个统计计算
Statistical Computing 的硕士,同时还修了很多统计系的博士课程。但要转去统计系念博士还是很费时的,经过多次咨询之后我决定放弃转系,在统计等系修了许多博士课程后,我最后还是返回到了社会学系来完成博士论文。
而在社会学系,我也还是得到了一些特别的学习机会,受益良多。我做过好几次社会学定量研究方法课的助教,也做了TUMA教授的助研而让我学到很多,特别是小区域数值估值的一些方法,尽管那不是我最感兴趣的。同时,我也为好几位教授做过数据分析的助研。其中有一位教授还曾说,我给他当助研而出来的文章是他这辈子发表的最好的定量分析文章。相对而言,斯坦福非常开放也经费充足,拿到博士资格后至少有五年时间不用担心资助问题,可以完全按兴趣发展。尤其是社会学系根据我以前的学习经历和研究方法与统计的相对高能力还免去了我必修的几门课程,这就给了我机会到统计系、计算机系和其它系去学习和交流,结果我修了一个统计计算
Statistical Computing 的硕士,同时还修了很多统计系的博士课程。但要转去统计系念博士还是很费时的,经过多次咨询之后我决定放弃转系,在统计等系修了许多博士课程后,我最后还是返回到了社会学系来完成博士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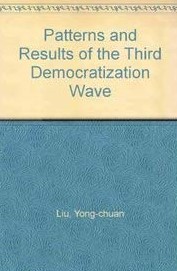 当时我最喜欢的方法一个是决策树方法,一个是结构方程和潜变量方法,为此就有点远离了社会学系的研究重心,也在社会学系找不到社会学方法的指导教授。好在斯坦福及那里的一些教授都很开放包容,特别是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的几位导师(包括担任过美国社会学会主席、也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
LIPSET 教授)对我非常包容和放手,我至今想起还很感激。尽管我的博士论文计划有点另类,但还是顺利获得了他们的批准。在做社会学博士论文时,考虑到导师的兴趣、可获得数据、当时热点等各因素,我选了政治民主转型作为应用的领域,使用了1970年代至1990年代的100多个国家的发展数据,并争取到了导师们的同意来应用我擅长的多种统计和数学模型。为此,我为博士论文还特别应用了决策树方法,虽然很初步,但由此我被认为是将决策树方法应用于政治研究的第一人。同时,我也应用了结构方程方法和潜变量方法,是比较前沿的探索,但在斯坦福没有碰到相关的专家,也就只成为了我独自的探索了。
当时我最喜欢的方法一个是决策树方法,一个是结构方程和潜变量方法,为此就有点远离了社会学系的研究重心,也在社会学系找不到社会学方法的指导教授。好在斯坦福及那里的一些教授都很开放包容,特别是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的几位导师(包括担任过美国社会学会主席、也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
LIPSET 教授)对我非常包容和放手,我至今想起还很感激。尽管我的博士论文计划有点另类,但还是顺利获得了他们的批准。在做社会学博士论文时,考虑到导师的兴趣、可获得数据、当时热点等各因素,我选了政治民主转型作为应用的领域,使用了1970年代至1990年代的100多个国家的发展数据,并争取到了导师们的同意来应用我擅长的多种统计和数学模型。为此,我为博士论文还特别应用了决策树方法,虽然很初步,但由此我被认为是将决策树方法应用于政治研究的第一人。同时,我也应用了结构方程方法和潜变量方法,是比较前沿的探索,但在斯坦福没有碰到相关的专家,也就只成为了我独自的探索了。
 回想起来,当时在统计系学习的最重要技术收获或许就是由决策树方法展开的对统计学习
Statistical Learning
的了解和研究,对于统计学习的钻研让我由此而进入了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并由此为后来的机器学习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学习与研究打好了特别的基础。在西北工业大学时,我兴趣在于应用数学来表达和解决社会问题,在北大后是开始从社会问题出发去寻求科技工具。到斯坦福后,大概是在统计系里呆的时间比在社会学系还多,好像又转回到应用统计计算来表达和解决社会问题、但更专更深入一些,也就是围绕决策树、结构方程的模型而通过统计学习做各种应用探索,社会学等方面知识则用来定义问题和解析分析结果。不过,走出社会学系还真让我成了一个跨学科的学者,也让我有机会认识了一些其它专业的大师,比如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等。
回想起来,当时在统计系学习的最重要技术收获或许就是由决策树方法展开的对统计学习
Statistical Learning
的了解和研究,对于统计学习的钻研让我由此而进入了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并由此为后来的机器学习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学习与研究打好了特别的基础。在西北工业大学时,我兴趣在于应用数学来表达和解决社会问题,在北大后是开始从社会问题出发去寻求科技工具。到斯坦福后,大概是在统计系里呆的时间比在社会学系还多,好像又转回到应用统计计算来表达和解决社会问题、但更专更深入一些,也就是围绕决策树、结构方程的模型而通过统计学习做各种应用探索,社会学等方面知识则用来定义问题和解析分析结果。不过,走出社会学系还真让我成了一个跨学科的学者,也让我有机会认识了一些其它专业的大师,比如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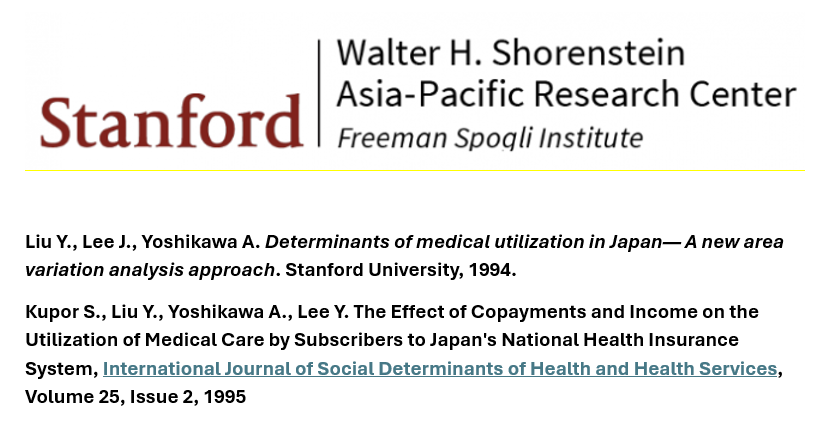 1992年3月31日完成全部学业工作后,我得到了一个
Stanford 博士后的位子,做健康医疗的数据分析模型,侧重美国与日本的比较研究。但我当时对健康医疗兴趣不大,不久就离开而转入了商业决策的应用,以后就基本将商业决策作为重点应用领域了,当然也关注医疗系统管理。后来,我在做应用的同时还在加州大学等校兼职教课,基本都在商学院里,应该也是由此而起的,但也或许和商学院研究更重视我喜欢的结构方程与潜变量方法有些关联。在方法上,当时比较花时间在决策树模型上,特别喜欢统计系
Jerome Friedman 等几位教授在 1984年出版的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后来,哈佛大学的统计学博士 Dan Steinberg
即以此书为基础,在他公司 SALFORD SYSTEM
里从1993年开始专门开发决策树模型分析软件并提供服务,还与我有些联系、合作。决策树模型及相关方法后来在机器学习等各方面应用得越来越广泛了,SALFORD
后来也并入著名的统计软件和数据智能公司 MINITAB,而公司的骨干则有人后来成为 AI
TRANFROMER (即 ChatGPT 技术基础)的奠基者之一。
1992年3月31日完成全部学业工作后,我得到了一个
Stanford 博士后的位子,做健康医疗的数据分析模型,侧重美国与日本的比较研究。但我当时对健康医疗兴趣不大,不久就离开而转入了商业决策的应用,以后就基本将商业决策作为重点应用领域了,当然也关注医疗系统管理。后来,我在做应用的同时还在加州大学等校兼职教课,基本都在商学院里,应该也是由此而起的,但也或许和商学院研究更重视我喜欢的结构方程与潜变量方法有些关联。在方法上,当时比较花时间在决策树模型上,特别喜欢统计系
Jerome Friedman 等几位教授在 1984年出版的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后来,哈佛大学的统计学博士 Dan Steinberg
即以此书为基础,在他公司 SALFORD SYSTEM
里从1993年开始专门开发决策树模型分析软件并提供服务,还与我有些联系、合作。决策树模型及相关方法后来在机器学习等各方面应用得越来越广泛了,SALFORD
后来也并入著名的统计软件和数据智能公司 MINITAB,而公司的骨干则有人后来成为 AI
TRANFROMER (即 ChatGPT 技术基础)的奠基者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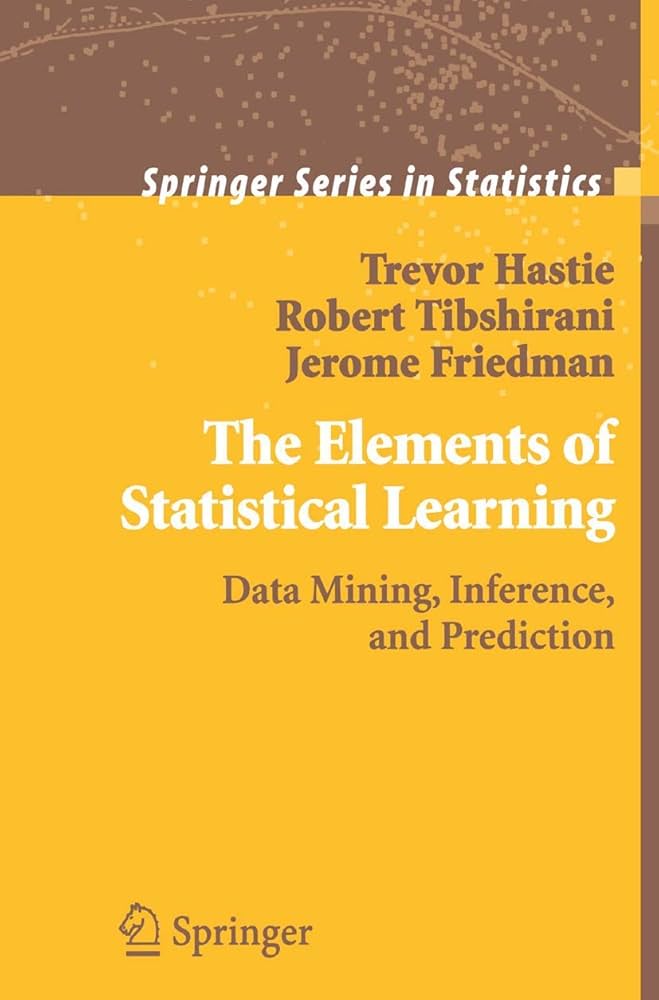 在斯坦福完成学业后,决策树方法、结构方程&潜变量方法以及统计学习非常确定地成了我的兴趣所在,应用方面在当时放在跨国比较分析多一些,因而与斯坦福的胡佛研究所等国际研究中心有些联系合作,但与斯坦福的社会学系就比较少有联系了。不过,与斯坦福统计系倒还是偶而会有些联系与合作,一直持续不断,且随统计系教授们在决策树与统计学习(机器学习)等方面的发展一起向前,特别是跟踪了
Jerome Friedman
等教授的工作。FRIEDMAN
等几位教授根据他们的教学与研究而整理出版的书 THE ELEMENTS OF
STATISTICAL LEARNING
一发行就是我的收藏,后来这本书成为了机器学习的经典教科书,也常常被我在IBM等机构使用,并在此基础上发展SPARK等技术上的应用实施。同时,我跟踪他们的发展、并偶尔参与也让我受益匪浅,顺利在统计学习、机器学习、人工智能上探索向前。为此,很多人都误以为我是斯坦福大学统计系或计算机系的博士,不相信我曾是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了。但是,我还是偏重应用和工程的,而且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的应用工作还是以社会与人群研究为主的。
在斯坦福完成学业后,决策树方法、结构方程&潜变量方法以及统计学习非常确定地成了我的兴趣所在,应用方面在当时放在跨国比较分析多一些,因而与斯坦福的胡佛研究所等国际研究中心有些联系合作,但与斯坦福的社会学系就比较少有联系了。不过,与斯坦福统计系倒还是偶而会有些联系与合作,一直持续不断,且随统计系教授们在决策树与统计学习(机器学习)等方面的发展一起向前,特别是跟踪了
Jerome Friedman
等教授的工作。FRIEDMAN
等几位教授根据他们的教学与研究而整理出版的书 THE ELEMENTS OF
STATISTICAL LEARNING
一发行就是我的收藏,后来这本书成为了机器学习的经典教科书,也常常被我在IBM等机构使用,并在此基础上发展SPARK等技术上的应用实施。同时,我跟踪他们的发展、并偶尔参与也让我受益匪浅,顺利在统计学习、机器学习、人工智能上探索向前。为此,很多人都误以为我是斯坦福大学统计系或计算机系的博士,不相信我曾是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了。但是,我还是偏重应用和工程的,而且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的应用工作还是以社会与人群研究为主的。 我1986年至1992年间在斯坦福大学的这段学术与研究经历,非常宝贵,为我后来在“社会科学人工智能(AI)”尤其是“健康医疗政策与管理人工智能”领域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跨学科的学习将社会科学、统计学和计算方法结合了起来,并有机会将决策树建模和结构方程技术应用于政治科学与民主化研究,开始练手。比较深入地学习统计学习理论,以及早期接触机器学习(统计学习)方法,为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复杂的社会与政策挑战奠定了不错的技术基础。此外,在建立协作性社区以及进行如美日医疗体系等比较政策分析时期的领导力锻炼,也准备了将数据驱动的洞察力与实际治理需求相结合的能力。
我1986年至1992年间在斯坦福大学的这段学术与研究经历,非常宝贵,为我后来在“社会科学人工智能(AI)”尤其是“健康医疗政策与管理人工智能”领域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跨学科的学习将社会科学、统计学和计算方法结合了起来,并有机会将决策树建模和结构方程技术应用于政治科学与民主化研究,开始练手。比较深入地学习统计学习理论,以及早期接触机器学习(统计学习)方法,为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复杂的社会与政策挑战奠定了不错的技术基础。此外,在建立协作性社区以及进行如美日医疗体系等比较政策分析时期的领导力锻炼,也准备了将数据驱动的洞察力与实际治理需求相结合的能力。
